2025年第39屆噶舉大祈願法會:法王第四天開示
- 詳細內容
- 分類:法王開示集
- 點擊數:414
# 2025年第39屆噶舉大祈願法會:法王第四天開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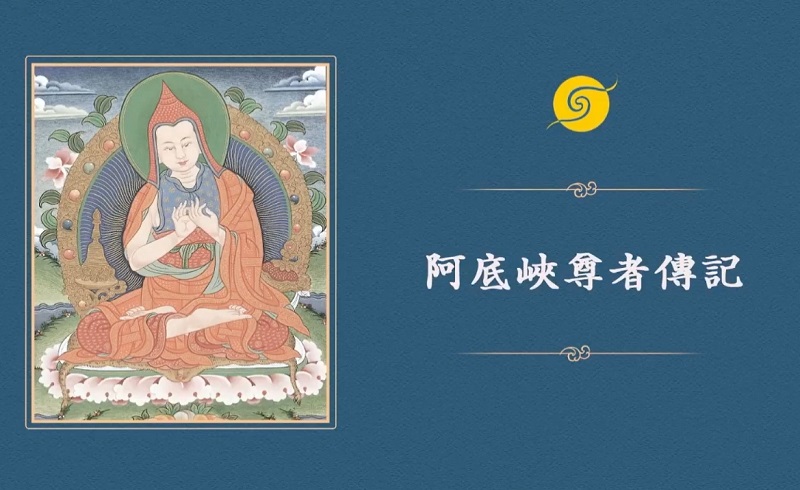
#「未獲神通前,莫多做弘法利生!」
主題:《阿底峽尊者傳》
主講: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日期:2025年2月8日(六)
藏譯中:堪布羅卓丹傑
▍十二,尊者入藏所說主要教法
(一) 先說「業因果」
阿底峽尊者抵達托林寺後,菩提光向他詳細陳述了藏地佛教的歷史:首先是古代藏王們如何在藏地引入並弘揚佛法,之後朗達瑪如何摧毀佛法,再後來自己的祖先們不顧生命危險重建佛法,但許多持有邪說的人使佛法變得混亂不堪。菩提光含淚陳述這些歷史,並懇請道:「請您在藏地教授因果業報之法,而不是那些過於深奧或稀奇古怪的法門。」
尊者聽了之後非常歡喜,回答說:「最深奧的法就是因果法。即便有人能夠見到本尊面容,如果能對因果生起堅定的信心,那才是最為殊勝的。在印度有一位修習大威德金剛的瑜伽士,因為見到了本尊面容,就認為『現在這樣就不會有過失了』,於是隨意使用僧團的財物,結果轉生為一個形象如同大威德的餓鬼。」尊者講述了許多類似的公案。
菩提光深深領會尊者的教導理念,而尊者也廣泛地為藏人們宣講因果業報的法門。據說,人們甚至尊稱他為「因果論師」,而這個名號本身就對佛法的弘揚產生了極大的幫助。
(二) 撰寫《菩提道燈論》
譯師仁欽桑布充分認識到尊者的殊勝功德後,便追隨尊者修學。他告訴所有人:「尊者在藏地只能停留一年,凡是想要求法的人都要抓緊時間。」在他的勸說下,拉尊菩提光供養了大量黃金,並向尊者陳述了當時藏地的困境:這裡有些人對佛法產生錯誤理解,因為沒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識,卻又不懂裝懂,製造許多虛妄之說。這些人互相爭論,各自臆測,做出許多違背佛法的事情。懇請尊者為他們消除這些疑惑。
除此之外,菩提光還向尊者提出了七個問題:兩個關於共同乘的問題、兩個關於波羅蜜多的問題,以及三個關於密咒的問題。他懇請尊者撰寫一部論著,要求這部論著能夠文字精簡但涵蓋佛法要義,並且結合尊者的修行體驗。同時,他還請求尊者依據佛智足所造的《密集續》口訣,撰寫一部以世間自在為壇城主尊的修法儀軌。菩提光恭敬地提出了這兩個請求。
尊者回應了菩提光的請求,他說:「藏地已有龍樹菩薩的《寶鬘論》,找不到比這部論典更殊勝的了。」同時他也提到已經有《普賢成就法》。之後,尊者撰寫了後來廣為流傳的《菩提道燈論》。
#宗喀巴大師說:《燈論》三大特點
這部《菩提道燈論》總共包含67個偈頌。根據宗喀巴大師在《菩提道次第廣論》中的闡述,這部論典具有三個重要的特點:
第一,顯密雙融:這部論典融攝了顯教和密教的精要,將二者的關鍵要義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因此內容十分完備。
第二,降伏自心:論典以調伏心識為主要修行次第,這使得修行者能很容易地將教法運用到實際修持中。
第三,二軌雙運:這部論典得到了兩位大師的加持:一位是精通龍樹菩薩傳承的日貝庫丘(རིག་པའི་ཁུ་བྱུག),另一位是精通無著菩薩傳承的金洲大師(གསེར་གླིང་པ)。這兩位大師分別代表了印度佛教的「二大車軌」傳承,因此這部論典比其他傳統的論著更為殊勝。
《菩提道燈論》的教授具有四大殊勝:能了解一切教法無有矛盾、能將一切經論視為修行教授、能輕易通達佛陀密意、能自然遮止重大過失。
因為尊者撰寫了這部論典,藏地的錯誤教法和密法誤用,不再需要透過直接或強制的方式來制止,這些錯誤自然而然就斷絕了。
#仲敦巴實修,《燈論》得弘傳
據說,雖然尊者寫了這部論典,但如果沒有像格西仲敦巴這樣的大師,這部論典就會像蓮花戒的《修習次第》三論一樣,只是在教理學院中講解而已。因為格西仲敦巴對論典內容進行修持、在心中生起證量,並且付諸實踐,所以《菩提道燈論》的純正教法才得以保存下來,這應該是仲敦巴的恩德。
有一次,有人對仲敦巴說:「如果《菩提道燈論》有一部註釋就好了。」仲敦巴回答:「這部論典沒有文字註釋。因為我是從作者本人那裡得到教法的弟子,所以我認為我自己就是註釋。」
簡單來說,《阿底峽尊者傳記廣錄》中提到菩提光向尊者提出七個問題,但具體是哪七個問題,典籍中並沒有明確記載。當尊者到達衛藏地區,庫鄂等人向他請教了五個問題,包括「方便和智慧分離是否能成佛」等。對此,尊者回答:「這些問題,拉尊菩提光問過更多,都記載在《菩提道燈論》中。」
其中,關於波羅蜜多的兩個問題和密咒的三個問題,庫鄂等人提出的內容很清楚,但是關於共同乘的兩個問題是什麼卻不明確。根據班禪洛桑曲堅的《菩提道燈論》註釋中提到,納措撰寫的《菩提道燈論釋‧解釋莊嚴》中,對這七個問題都有逐一說明。
我看過一些噶當派祖師撰寫的《菩提道燈論》早期註釋,其中有些提到五個或六個問題,並且都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些問題和回答的對應關係。雖然現在這種講授方式不太常見,但正如班禪洛桑曲堅所說:「這些註釋不僅對論典解釋得很細緻,而且對初學者的修持方法也極為殊勝。」我在讀這些註釋時,確實感受到它們有特別之處。至於《菩提道燈論》是否有自註,以及阿底峽尊者前往衛藏的具體情況,因為今天時間有限,就無法詳細說明了。
▍十三,尊者返回藏地的因緣
(一) 三年期滿預計返回印度
我們提到過,在阿底峽尊者前往藏地之前,納措譯師曾向超戒寺的住持長老立下重誓:「三年之後,我一定會恭送尊者返回印度。」當三年期限就快到了的時候,納措譯師實在想不出其他辦法,只好請求尊者返回印度。
尊者考慮之後,也同意了這個請求。後來,尊者和隨行人員來到了布讓。在那裡,菩提光又再次懇切地請求尊者傳法。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尊者撰寫了《求解脫勇士心要》這部重要的論著。
(二) 度母授記,利益主要弟子仲敦巴
前面說過,當阿底峽尊者還在印度的時候,至尊度母就曾經授記,如果尊者去藏地的話,會對一位在家人特別有幫助。這位在家人是誰呢?他就是後來成為阿底峽尊者最有名的弟子——仲敦巴。
很多歷史文獻都記載了仲敦巴第一次見到尊者的情形,這件事是在尊者到達布讓之後發生的。尊者雖然一直記得度母的授記,但一路上都沒有遇到特別的在家人,所以心裡有些遺憾。到了布讓以後,度母又一次授記:「一位大居士很快就會到來。」於是尊者每天都在期待著這位居士的到來。
那麼,當時仲敦巴在哪裡呢?他最初是住在康區的。他在康區聽聞了阿底峽尊者的名聲之後,就從康區一步步往這邊走,來到了布讓。當他到達尊者寢室附近時,尊者應施主的邀請出去,還沒有回來。在尊者寢室的人們對仲敦巴說:「請稍等,尊者很快就會回來。」可是仲敦巴說:「見善知識應該立即去見,一刻也不能等待。」說完,他就朝著施主家的方向跑去。
奇妙的是,就在這個時候,阿底峽尊者正好也從施主家往回走,兩人在一條狹窄的路上相遇了。一見面,仲敦巴就向尊者作了五體投地的大禮拜。尊者也非常歡喜,將手放在仲敦巴的頭上,用梵語說了許多吉祥的話。當時的情景,就很像阿底峽尊者當年遇見金洲大師的情形。
由於仲敦巴精通梵語,所以他們之間的交談和溝通完全沒有任何障礙。從相見的那天晚上開始,阿底峽尊者和仲敦巴就住在同一個房間。雖然戒律中規定在家人和出家人不能同住一處,但因為阿底峽尊者是從大眾部出家的,按照大眾部的規矩,只要在他們的床鋪之間掛一道簾子就可以了。
(三) 在尼泊爾遭遇戰亂阻礙
納措譯師一直想繼續護送尊者返回印度,但當時尼泊爾發生戰亂,無法前行,只得暫時返回藏地,打算等待戰亂平息後再啟程。這使納措譯師十分憂心,尊者安慰他:「不要擔心,這不是你沒盡力,而是盡力後情況未如所願。我們可以寄信去印度說明情況。」
於是尊者寫了一封信,連同《菩提道燈論》手稿和一些黃金一起寄往印度。至於這封信到達印度後,諸位學者研討《菩提道燈論》的經過,今天因為時間關係就不詳述了。
當時,實際上很多藏人都希望尊者不要返回印度,留在藏地,但沒人敢直接提出請求。然而,多虧了足智多謀的仲敦巴,不過他也不敢直接開口請求尊者留下,就天天在尊者耳邊說:「中藏地區有多少多少寺院,多少多少僧眾。」尊者一聽就非常歡喜地說:「現在連印度都沒有這麼多僧人,這是非常難得的。如果我去了能讓他們歡喜的話,我會考慮去中藏。因為我此生已立下誓願要遵從僧眾的指示。」
(四)仲敦巴敦促衛藏大德,迎請尊者住藏
仲敦巴知道這個消息以後,便寄信給衛藏地區的顯貴和高僧大德們,勸請他們迎請尊者前往衛藏。
信中,仲敦巴具體列出了許多在衛藏有影響力的大師的名字,例如菩提王和鄂勒貝謝饒等。
當這封信送達衛藏後,諸位顯貴和大師們召開會議討論此事,並且達成了共識。不過,因為仲敦巴在信中忘記提到庫敦的名字,所以會議沒有邀請庫敦參加。庫敦對此感到不悅,心想:「你們既然這樣輕視我,那我就先去迎請尊者。」於是他帶著一群人騎馬出發,往阿里方向去了。不久之後,衛藏其他的顯貴和高僧大德們也踏上了行程。
當時,阿底峽尊者和隨從們從阿里出發,往南方行進。當他們接近衛藏地區時,藏地的大師們身穿氆氌大衣、戴著帽子,騎著馬,聲勢浩大地前來。尊者是印度人,從未見過這樣的裝扮,驚呼:「有鬼!是藏地的鬼!」隨即用法衣蓋住頭部。庫敦的隨從們看見尊者受到驚嚇,立即換上如法的黃色法衣來迎請,尊者這才安心。此時尊者帶著愉悅的微笑向他們回禮,並說:「藏地僧人的生活條件和衣著,比印度的比丘還要好呢。」
當時因為前來迎請的人很多,庫敦生氣地跑到仲敦巴面前質問:「你寫給衛藏著名人士的信中,為什麼沒有寫上我的名字?」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質問,仲敦巴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便說:「我有寫到您的名字啊,在『鄂譯師等』這個『等』字中包含了您。」聽到這話,庫敦更加憤怒,大聲說:「像我這樣的大人物,豈能放在『等』字之中?」從那時候起,庫敦對仲敦巴產生了不滿,兩人之間有了嫌隙。
之後,當阿底峽尊者在前往衛藏的路上想要唱誦道歌,仲敦巴說這不適合藏地的人,於是尊者略感遺憾地停止了。據說,仲敦巴之所以要阻止,是因為當時密續的錯誤修持十分普遍,而尊者是為了淨化教法才被迎請來藏地的,如果這時講授如此甚深的密法,恐怕人們會誤用。然而,從長遠來看,許多大成就者都說過,阿底峽尊者精通密法,但未能好好解釋密法的教義,這對藏地是一個重大的損失。例如,尊者密勒日巴曾對岡波巴說,「是藏地的愚人們不讓阿底峽尊者講授密法」,這句話可能就是指這件事。
(五) 前往桑耶寺並讚歎大覺佛像
阿底峽尊者66歲時(公元1047年)來到衛地,前往桑耶寺。傳說,當尊者參觀桑耶寺,看到主尊大菩提釋迦牟尼佛像後讚歎:「這尊佛像與菩提迦耶正覺大塔的佛像極為相似。」當時,許多藏地學者聽聞尊者抵達桑耶寺,都前來請求他講解《二萬頌般若》。
(六) 選擇常住地點
當時,仲敦巴考慮要為阿底峽尊者選擇一個理想的長期住處。有四個選擇地點:一是雅礱,二是桑耶,三是拉薩,四是聶塘。其中以龐敦所在的聶塘地區最為理想。基於這個原因,仲敦巴寫信給龐敦說:「您所在的聶塘地區地理優越,氣候宜人,最適合作為尊者的常住處。因此請您迎請尊者到聶塘。」龐敦收到信,認為仲敦巴說得有理,便向大家宣布:「這次阿底峽尊者不去其他任何地方,我負責迎請尊者到聶塘。」
然而,仲敦巴沒有料到,庫敦私下對阿底峽尊者說:「如果像仲敦巴或龐敦這樣的人來供養您的住處和生活條件,您就沒有機會利益眾生了。像我這樣的人有能力和條件好好服侍您。而且,我居住的雅礱地區曾是許多贊普的駐地,地理優越,山水秀麗,您可以在這裡利益很多人。此外,我會為您安排冬夏兩處住所,保證冬暖夏涼。」
(七) 在唐波齊講法
之後,阿底峽尊者和仲敦巴分道而行。仲敦巴和龐敦前往聶塘,尊者則與庫敦的迎接隊伍一起去了雅礱。到達雅礱後,尊者一行住在唐波齊這個地方。在那裡,尊者講授了《二萬頌般若》和它的註釋、《究竟一乘寶性論》、《辨法法性論》等許多教法。同時與納措譯師一起翻譯了許多密續典籍。
然而,當尊者住在唐波齊的時候,庫敦很多事情都沒有按照尊者的意思去辦,因此尊者一行人,可以說是過得十分辛苦,甚至有時候連人帶馬七天都吃不上飯。
(八) 從雅礱逃離
當時仲敦巴住在聶塘,時常掛念著尊者的情況,便對龐敦說:「我們必須迎請尊者到聶塘。庫敦性格傲慢,不會好好承事。因此我先去雅礱察看情況,設法將尊者迎請到桑耶,然後你派人從桑耶迎請。」兩人歡喜地達成共識後,仲敦巴便前往雅礱。
當仲敦巴接近唐波齊時,將近日落。他首先尋找一位認識的庫敦弟子,詢問尊者的住處。然而庫敦的弟子們對他不予理會,不告知尊者的住處。就在這時,仲敦巴遇到一位印度籍的尊者弟子,尊者弟子一見到仲敦巴就非常歡喜,帶他到尊者的住處。
尊者在唐波齊雖然只住了一個多月,但看上去卻像經歷了一年多的苦難般,身形消瘦,顯現出極為困頓的樣子。尊者一見到仲敦巴就說:「大居士,請快些帶我離開這裡。我們都很辛苦,連這些馬也都是可憐的眾生啊。在這裡,庫敦像轉輪王一樣享有三十三天的享受,而我卻如同一個普通的乞丐。」說著便哭了。
仲敦巴說:「如果想去一個好地方,我有個很好的建議。有個地方叫聶塘,那裡有許多樹林草地,即便在冬天也會開花。」尊者立即歡喜地說:「居士,那我們現在就走吧。」仲敦巴回答:「那不行,絕對不行。庫敦是大人物,我們必須想個好辦法逃走。」尊者說:「不要擔心,我有他不知道的方法,我們現在就走。」於是他們連夜收拾行李,在黎明時分逃離。
他們逃離時被庫敦的一位弟子看見,立刻趕去稟報庫敦。奇怪的是,那天庫敦住處的早課用了比平常更多時間。通常庫敦早上會出外散步,但那天庫敦卻反常地沒有出門,還說有事情要做並關上了門。那位僧人著急地敲門,大聲喊道:「您關著門在做什麼?仲敦巴已經把尊者帶走了!」庫敦一聽驚訝不已,立即衝了出來,準備好馬匹和人手去追趕。
因為庫敦富有,他有一匹名叫唐納的良馬。平常他一呼喚,唐納就會立即來到他面前,但那天卻很反常,不管庫敦如何呼喚,唐納都只是來回奔跑,誰也抓不住。最後眾人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勉強抓住唐納,然後大家騎上馬,追趕尊者一行人。
(九) 河邊道別
當尊者一行人在日出時分抵達河邊時,需要乘船渡河。藏地的船是用犛牛皮製成的小皮船,容納不下太多人。仲敦巴向尊者請求道:「請讓我先渡河,否則若等到庫敦來了,他會打我。」這樣說著,他先上船擺渡到了對岸。
船一返回,尊者才剛要登船,遠處就揚起陣陣塵土,庫敦率領的追兵趕到了。庫敦騎著唐納馬,領先眾人抵達,他高聲說道:「您不對侍者們說一聲就要離開,是要拋棄我嗎?」尊者回答:「你也沒有拋棄我啊,藏地的大學者,現在請你回去吧。」
就在此時,庫敦到達河邊,但他的唐納馬卻失控了,使他跌入河中,就快要被河水沖走了,幸好路人跑來相救,愛他的弟子們將他救起後,庫敦繼續說:「尊者,您這個不知感恩的印度人,我們好好談談不行嗎?」尊者懇求道:「大學者,請不要這樣說。」
最後,庫敦無計可施,便說:「那麼,請給我一件供養的紀念物吧。」於是尊者摘下自己的法帽,拋向河面,贈與庫敦。庫敦接過法帽,與眾人一起頂禮後,便從河邊返回。
(十) 尊者住在桑耶
尊者從雅礱來到桑耶之後感到非常歡喜。主要是因為在桑耶有許多梵文經典,特別是眾多密續典籍。他說:「從前我以為見過所有的續部,但現在看來並非如此。續部確實如大海般浩瀚。印度寺院曾三次發生火災,許多經典因此毀於大火,許多經典在印度已經完全失傳。然而在這裡還能見到這些經典。」在桑耶期間,他有時研讀經典,有時繞寺巡行。後來他召集眾多弟子,抄寫了大部分經典寄往印度。
尊者本想在桑耶長期住留,但是因為拉尊菩提王既是國王又是上師,他的一些眷屬對尊者生起嫉妒,因此尊者無法在桑耶長住。之後,龐敦派遣二百多人馬迎請尊者前往聶塘。從桑耶到聶塘的途中,尊者來到拉薩。在那裡,他的三大重要弟子之一的鄂勒貝謝饒迎請了他。在拉薩期間,鄂勒貝謝饒等許多人向尊者求受諸多灌頂和傳承,同時他們也翻譯了《度母修法》等眾多密續典籍。特別是應鄂譯師的祈請,尊者還翻譯了《中觀心要疏‧理光焰》等論著。
▍十四,尊者晚年與圓寂
(一) 尊者晚年
當尊者到達聶塘後,與納措譯師一起翻譯了許多顯密典籍。雖然尊者對於在藏地弘揚佛法有諸多計劃,但許多願望未能如願實現。
1.無法弘揚大眾部戒律
尊者觀察到說一切有部對飲酒過失比較寬鬆,而大眾部的酒戒等較為嚴格,因此想在藏地弘揚大眾部的戒律傳承。然而有兩個原因使這個想法無法實現:其一,是藏地諸位君王立下誓約,規定戒律只能從有部傳承;其二,是因為在印度各部派之間有重大爭議,擔心這種情況也可能在藏地出現。因此,仲敦巴向尊者請求不要授予戒律,並加以阻止。
2.無法直接宣講密法
尊者還想弘揚密續和口訣,但仲敦巴請求他不要直接宣講密法。據說尊者因此感到失望,說道:「那麼,我來藏地有什麼意義呢?」根據《達波仁波切傳》記載,與仲敦巴大約同時期的密勒日巴尊者也曾對岡波巴說:「藏人心中入魔,不讓阿底峽講授密法,正因如此,噶當派雖有一些密法,但缺乏口訣。」
3.開啟每日供水的傳統
當尊者來到藏地,年近七十,邁入晚年時,大多時間不再講法,只是偶爾會唱誦道歌,這些道歌後來被譯成藏語。閒暇時,尊者會在寢室附近散步巡行,觀賞藏地的山水花草等。他特別讚歎藏地清澈的水,曾說過:「在藏地只需供奉清水,便能積累福德。印度因為天氣炎熱,沒有像藏地這樣的清涼泉水。」因此尊者每日都供奉淨水。據說,我們現今供水和獻水的傳統,也是源自於尊者。
4.慈悲憐愛小動物
每當見到受苦的動物,尊者會問:「小羊可好?小馬可好?」等。他特別喜愛小狗,見到時會把牠們抱在懷中,說道:「小狗可好?得此劣身,是你自己的過錯啊。」顯露極大的慈悲心。
(二) 尊者圓寂
後來尊者臨近圓寂,召集親近的弟子們到跟前,一一給予教誨。他對弟子們說:「將來我不在,因為我已經加持過他,你們要依止上師仲敦巴。」
仲敦巴問道:「若您不在,我應該依止誰呢?」尊者回答:「我不在了以後,你要以經典為師。在未獲得神通之前,不要做太多利他事業。除此之外,要盡力弘揚佛陀的教法。佛法的興衰取決於僧團,而僧團的興衰則取決於持戒清淨的比丘們。因此,將來你要培養眾多持戒清淨的比丘。」等等教言。當一些弟子詢問該如何安置尊者的舍利?尊者說:「按照《涅槃經》中記載處理佛陀舍利的方式來做就可以了。」
尊者圓寂以後,在聶塘舉行荼毗。荼毗之後要保存舍利灰,庫敦在所有人正在享用午齋時,拿著一個鐵盒說:「如果我現在不取的話,之後仲敦巴會將所有的舍利灰都帶走,我連一點點也得不到。」這樣說著,便取了一些舍利灰。後來庫敦用這些舍利灰製作了許多擦擦,將它們安置在藏地幾個不同的地方,因此尊者的舍利可說遍布藏區,這是庫敦的恩德。
▍十五,阿底峽尊者的影響
(一) 注重戒律
由於阿底峽尊者傳承的是屬於大眾部的戒律,但是受限於種種原因,他在藏地未能廣泛弘揚這個傳承。然而,當他來到藏地,雖然正值密法廣泛流傳的時期,他卻特別強調持守戒律的重要性,這使得藏地各大教派都以出家僧團作為傳承核心。
(二)強調皈依
當時有許多自稱是大德善知識和具有高深證悟的密咒師、瑜伽士們,阿底峽尊者指出,他們對皈依的理解和觀念都很不清楚,甚至說這些人很難被稱為佛教徒。因此,尊者特別強調皈依的重要性。正因為這個緣故,藏地形成了現在這種修行傳統:即使我們只修一個四句偈,也一定要從皈依開始。
(三)重視因果
在阿底峽尊者到達藏地之前,有許多人談論空性和大圓滿等深奧法門,卻對因果不以為意。阿底峽尊者教導:「修行人的見地愈高,就應該愈發謹慎對待因果。」正是這樣的教導,在藏地形成了一個傳統:不論修學的是哪一乘的法門,所有修行人都極為重視因果。
(四)弘揚菩提心
此外,在藏地,大乘佛法的根本——菩提心的修習傳統和口訣,都源自阿底峽尊者的教導。在藏地,受持菩提心戒的儀軌有兩大傳承:一脈是從龍樹菩薩傳下來的,另一脈是從無著菩薩傳下來的。這兩大傳承通常被稱為「甚深見派」和「廣大行派」。其中,龍樹菩薩傳承的甚深見派是由於阿底峽尊者的恩德而在藏地弘揚開來。可說是仰賴阿底峽尊者的恩德而成就的。
同樣,在藏地,中觀應成見的廣泛弘揚也是阿底峽尊者的恩德,這是因為最早翻譯月稱論師的《入中論》並宣講應成見的大師,就是阿底峽尊者。由於依止阿底峽尊者,《般若經》的詮釋也得以弘揚,因此形成了所謂的「般若康派」等傳統。據說,最早在西藏宣講《究竟一乘寶性論》的也是阿底峽尊者。
(五)廣弘藥師佛暨度母法
在諸多顯乘儀軌當中,在藏地傳播最為廣泛的是藥師佛儀軌。談到藥師佛儀軌的來源,通常會提到兩個傳承:其中一個是前弘期由寂護大堪布傳下來的,另一個是後弘期從阿底峽尊者傳下來的。據噶瑪洽美等大師所說,很早以前,各寺院就以藥師佛儀軌為主要誦持儀軌,這是源於阿底峽尊者的貢獻而成就的。
不僅如此,聖救度母法門的廣泛弘揚也主要是阿底峽尊者的恩德,因為救度母的法類雖然在前弘期就已經傳入藏地,但似乎在後弘期更為興盛。在後弘期,最早且最重要的以救度母為本尊的印度上師,就是阿底峽尊者。
不僅如此,藏地各處供水的傳統,據說也是阿底峽尊者所創立的。
(六)開創噶當派,四大傳承皆修持
阿底峽尊者對藏地最大的貢獻是:因其開創了名為噶當派的特殊教派。雖然這個教派只維持了幾個世紀,但噶當派上師們以善心和清淨行為聞名,受到藏地各教派的尊重,並成為最受歡迎的教派之一。
這個教派與其他教派有什麼不同呢?噶當派的上師們終其一生修持菩提心、慈悲心、愛他勝自、知足少欲、修心、施受、安住當下、只為來世著想等,每一個法要都是佛法的精髓,他們畢生修持這些法要,因此這些上師們都成為了無與倫比的聖者。
在噶當派的上師中,鄂勒貝謝饒創建了桑浦寺,這成為了藏地一切教法學習的源頭。夏惹巴的弟子東敦洛追扎巴創建了納塘寺,後來編纂了《甘珠爾》和《丹珠爾》等,對整個藏地的恩德無法衡量。
從某個角度來說,達波噶舉也持有噶當派的傳承。根據拉欽貢嘎嘉參所著的《噶當教法史明燈》:從法王岡波巴開始被稱為達波噶舉的傳承,也是修持從阿底峽傳下來的教授。法王岡波巴和怙主帕摩竹巴也都著有道次第論著。
直貢法脈的特色,是在見地和行持兩個傳承上,都傳承自阿底峽師徒主張三律儀要次第學習、以皈依區分佛教和外道的差別、認為業因果比氣脈等更為深奧、視持戒為殊勝行為等,這些都是噶當派的特殊甚深法要。洛喇雅巴所著的《四法論》中,前三法顯然是三士道次第,這也是持守阿底峽的教授。
因此,岡波巴師徒們以道次第為基礎,尊者(密勒日巴)修持拙火等方便道,這就是所謂的「噶當大印二脈合流」。後來至尊宗喀巴大師也是以阿底峽的三士道次第為波羅蜜多道的根本,而密咒的深要則取自殊勝者瑪爾巴的教授。正因為如此的,格魯派也持有阿底峽的教法傳承,因此被稱為新噶當派。
吉祥薩迦派最初也是由阿底峽預言其道場,在五祖中的尊者索南哲莫曾在桑浦寺等噶當派寺院學習。薩迦派出現眾多著名學者,也是源於在噶當派寺院學習的傳統。
總之,薩迦、格魯、噶舉、寧瑪諸派的上師無論是誰,幾乎都不可能不修持噶當教法。因此,如今在藏地雖然噶當派不再單獨存在,但沒有一處不為噶當教法所遍及。這是因為在藏地的顯密二者中,顯教方面的經典學習和口訣,無一不是從噶當派傳承而來。因此,了解並緬懷阿底峽師徒的恩德極為重要。